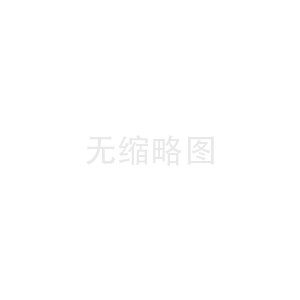恐怖女鬼短视频_游戏论|性别视角下的中式恐怖游戏“女鬼”形象探析,一看就会
“中式恐怖游戏”堪称国产游戏中的佼佼者自《纸嫁衣》、《烟火》等作品问世以来,这种游戏风格在各大平台引发了广泛讨论每一部打着“中式恐怖”旗号的游戏作品都备受国内玩家关注,对这一风格的研究与探讨也层出不穷然而,随着《黑神话:悟空》等国产3A游戏的崛起,“中式恐怖游戏”的热度逐渐被新概念所超越。
当下,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中式恐怖游戏”时,新玩家对这一风格的评价已变得褒贬不一然而,口碑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游戏类型的否定,而是提醒开发者与研究者,现有的“中式恐怖游戏”已无法满足玩家的审美需求,对这一风格的探讨需要更加深入。
在这些新的批评声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对中式恐怖游戏中符号复制的批判诸如“纸人”、“冥婚”、“丧葬”等元素,以及凄美的爱情与被压迫的女性形象,这些自我复制的符号使得中式恐怖游戏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停滞玩家们发现,这些反复使用的恐怖符号——无论是作为事件的“冥婚”、“殉葬”,还是作为物品的“红盖头”、“绣花鞋”——都指向了同一个形象:“封建时代的女性”。
这种对“封建女性苦难”的反复呈现,成为中式恐怖游戏中的核心主题正如戴锦华所言:“在恐怖片中,一个女鬼似乎比一个男鬼更自然,同时更可怕”这引发了部分玩家对中式恐怖游戏“虐女叙事”的不满他们抱怨这些游戏总是反复咀嚼女性的苦难,并将其一遍遍展示给玩家。
这种批评不仅针对平庸之作,也指向曾经备受赞誉的作品正如当下的影迷对“老派电影”的厌倦一样,它提醒我们,新一代玩家已经厌倦了在游戏中经历无尽的“冥婚”、“殉葬”和“家暴”玩家迫切呼唤国产游戏在“中式恐怖”领域的新想象与表达。
一、“女鬼”养成法:“恋爱女鬼”与“复仇女鬼”作为以“民俗”为卖点的游戏类型,中式恐怖游戏在符号还原和形象塑造上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前代的文化遗产在这些遗产中,“女鬼”是一个极其经典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如古典时期的《搜神记》中的“苏娥”、《聊斋志异》里的“聂小倩”、“梅三娘”,以及当代港台恐怖片中的“山村老尸”。
女鬼的身影无处不在,游走在每一个名为“中式恐怖”的角落根据洪鹭梅、刘相雨等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古典作品中的“女鬼形象”分为两类:“恋爱女鬼”与“复仇女鬼”这两类形象分别对应传统志怪中的两种叙事模型:“人鬼之恋”与“女鬼复仇”。
在前一种模型中,“女鬼”通常不具备太多恐怖元素,充其量只是一个“被替换的能指”她们具备所有古典小说赋予“完美女子”的特征:温柔、美丽、知书达理,并期待与主角展开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而后一种模型中的“女鬼”则更加凶猛、更令人恐惧。
她们生前往往遭遇过诸多不公与压迫,死后怨气未消,化为厉鬼,通过诱惑或暴力向他人复仇这种古典叙事模型在当代并未失去其生命力事实上,大部分中式恐怖游戏中的“女鬼”形象仍然基于这两种模型生成《烟火》中的陈青穗、《三伏》中的邱芜是对“恋爱女鬼”的当代改写;《港诡实录》中的蜘蛛怪陈伶宜和红衣女鬼则是“复仇女鬼”的典型代表,而《纸嫁衣》系列则两者兼具。
然而,隐藏在这一“生命力”背后的是一个悠久的叙事传统:“只有男性才拥有讲故事的权力”古典文本中的叙事主体无一例外都是男性,或者说,正是传统的“父权秩序”创造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女鬼”形象这意味着,无论是“恋爱女鬼”还是“复仇女鬼”,都反映着创作主体的欲望。
S.M.吉尔伯特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将西方自古典时代以来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类:“房间里的天使”与“阁楼上的疯女人”在吉尔伯特的论述中,“天使”意味着由父权制主导的传统社会所塑造出的完美女性形象,而作为对立面的“疯女人”则指那些试图抛弃这一“完美”形象,被判定为“疯癫”与“危险”的女性。
“阁楼上”这一修饰语也暗示了这类女性的命运:她们被指控为“疯子”,作为“异质物”被监禁在远离日常世界的“阁楼”中这一叙事中,世界被分割为三个部分:供男人们冒险、创造的“外界”,供“天使”们梳妆打扮、生儿育女的“房间”,以及用于监禁“疯女人”的“阁楼”。
前两者构成了传统秩序下的“日常空间”,而“阁楼”则是流放和监禁危险之物的“异质空间”正是“阁楼”的存在界定了“日常”的边界,规定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正常”就像“天使”与“疯女人”分别锚定了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不同位置,中式恐怖游戏中的“恋爱女鬼”与“复仇女鬼”也体现了“圣女”与“恶女”的二元对立。
对于玩家来说,“恋爱女鬼”是日常的、无危险的,甚至是游戏中的完美理想因此,她们通常作为主角(通常是男性)的同伴或助手登场例如在《纸嫁衣3:鸳鸯债》中,死去的王娇彤表现出“可爱俏皮”的形象,完全脱离了“女鬼”应有的恐怖特征,与游戏中的其他女性角色无异。
可见,“恋爱女鬼”的“非危险性”在于她们被塑造为辅助男性形象,她们的存在更像是为了给主角一个完美的异性配偶,而她们只有依托于对男性的“爱”才能存在在这一维度上,“女鬼”与其他女性角色的塑造逻辑一致:她们都是传统两性观念下的派生物,因此天然地成为男性的“天使”。
《纸嫁衣3:鸳鸯债》中的女主角“王娇彤”作为其对立面的“复仇女鬼”则是玩家在游戏中必须面对的危险“异质物”、“疯女人”这类女鬼通常不具有“恋爱女鬼”的姣好面容与可爱性格,更多呈现为怪物般的恐怖外形她们没有传统道德与善意,唯一的功能便是对目标进行攻击。
例如在《港诡实录》中,化身为女鬼的嘉慧拥有猩红的双眼与血盆大口,追上主角后会突然冲到屏幕前,给玩家带来强烈的惊吓同样出现在《港诡实录》中的花旦陈伶宜则是人头蛛身的蜘蛛怪形象,而在《还愿》中,主角杜丰宇在恐惧中看到的妻子也不过是一个四肢扭曲向他爬行的诡异怪物。
玩家在游戏中的任务便是通过一系列规则与玩法对这些危险的异质物进行“驱魔”在中式恐怖游戏中,“驱魔”意味着玩家对已经“异质化”的“日常空间”进行“净化”,使其重回“日常世界”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作为“异质物”的“女鬼”的驱除。
在《港诡实录》、《纸人》、《女鬼桥》等包含追逐战斗系统的中式恐怖游戏中,这种“驱魔”表现为玩法上的暴力攻击——玩家对“复仇女鬼”的驱除正是将作为“异质物”的“疯女人”关入阁楼的过程异质物的属性决定了她们要么被改造后重新纳入日常秩序,要么被彻底驱逐出日常世界,即“净化”与“毁灭”的二选一。
因此,作为其产生原因的“悲惨身世”只能化为一个意义不大的背景要素这种割裂在《港诡实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玩家在前期的线索搜集中已了解陈伶宜与红衣女鬼生前的悲惨身世;另一方面,玩家又不得不在后续的战斗中将这些已经怪物化的女鬼予以消灭。
类似的矛盾同样出现在其他游戏作品中
【星界云手机】让你的游戏时光更加充实!云端托管手游,无需担心设备性能、电量损耗等问题,随时畅玩游戏。搭配挂机脚本,让你的游戏之路更加轻松、高效!
《港诡实录》中的红衣女鬼对于“恋爱女鬼”来说,尽管她们在躯体上仍然表现为“女鬼”这一非日常之物,但由于她们已被纳入日常生活所规定的两性秩序中,因此不具备任何危险性或异质性因此,她们的命运要么如同《烟火》中的陈青穗或《三伏》中的邱芜,在游戏的最后主动选择消失,成为玩家心中的“意难平”;要么,就像在《纸嫁衣》系列为代表的“男女双主角”模式游戏中那样,即使有重要的女角色死去,也必须和王娇彤一样以“女鬼”的身份再度归来,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在这一系列矛盾中隐现的正是“中式恐怖游戏”中的悖论:以“反封建”为基本主题的游戏文本在形象塑造上却沿袭了封建时代的父权想象对古典叙事模型的继承导致游戏文本中出现了一道吊诡的裂痕:如果游戏中“女鬼”的诞生正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创伤与压迫,那么为何消灭女鬼的方法却是使“异质空间”重新回归“日常”?。
在德国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的画作《大使》中,画面的前景处放置着一个被斜向拉长的扭曲物体,从侧面望去才能看清它的真实样貌:“一个倾斜的骷髅”这个只有“斜目而视”才能看清的符号构成了整幅画的最大隐喻:“对世俗权力的死亡凝视”。
同样,为了理解中式恐怖游戏中的这一悖论,或许我们也需要暂时放弃已经习惯的直视目光,转而以一道倾斜的目光,重新进入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符号中,从而真正地回答:“什么规定了我们的恐惧?”“在这些‘女鬼’的身影中,那些始终被试图压抑的恐惧之物究竟是什么?”。
小汉斯·荷尔拜因《大使》二、“斜目而视”:游戏中的“恐惧”与“驱魔”1487年,在教皇英诺森八世的默许下,多明我会修士海因里希·因斯蒂托里斯和雅各布·斯普伦格出版了欧洲猎巫运动的指南《女巫之锤》在这部作品中,巫术的起源被解释为“那些淫欲无节制的女性,她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而与魔鬼交配”。
因为“女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很脆弱,会因淫欲不满而躁动,极易成为魔鬼的猎物”通过与魔鬼的交合,女巫们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神秘力量在这部臭名昭著的著作中,我们得以窥见传统社会认为应当被驱逐的两种女性特质:“诱惑”与“力量”。
正如猎巫运动中,“女巫”往往被描述为兼具这两种特质的危险女性,她们一方面诱惑男人,影响女人,从而破坏家庭;另一方面则通过魔鬼的力量对普通人的身体造成伤害无独有偶,这一“诱惑”与“力量”的双重性同样显现在中国的“女鬼”形象中。
在一系列有关女鬼的古典志怪中,最为流行的叙事模式之一便是“主角遇到了幻化为美女的女鬼,在被其诱惑后付出了某种代价”与欧洲的“女巫”相似,作为“异质物”的“女鬼”镌刻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幻想,同时也构成了对这一幻想的符号性遏制,即“女鬼”的身体一方面象征着性的诱惑,另一方面则昭示着性的恶果。
“诱惑”与“禁忌”的共轭性在部分港台中式恐怖游戏中尤为明显例如在《港诡实录》中,作为女鬼的“嘉慧”既是张着血盆大口追逐玩家的恐怖怪物,又是身材姣好的年轻女孩而嘉慧的服装则是高开叉的设计,使得玩家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窥视到嘉慧裙底。
“女鬼的诱惑”构成了一种对传统两性秩序的反叛依照“人鬼恋”的叙事模型,“女鬼”只有依托于对特定主体的爱才能存在,“爱”这一行为甚至可以决定她生命的状态,使其起死回生而在“诱惑的女鬼”中,这一秩序彻底颠倒——不仅“人鬼恋”中一对一的“忠贞爱情”被转化为了一对多的纯粹诱惑,“女鬼”也不再是被吸引的客体,而是一具自发吸引对象的主体。
在这一颠倒的叙事中,男性失去了确定自己配偶的权力,而沦为众多“被诱惑者”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情欲”不再是男性的特权,反而幻化为男性无法掌控的危险力量因此,在传统叙事中,为了使这一诱惑无害化,女鬼要么在后续的情节中成为主角的恋人,即将“诱惑女鬼”重新转化为“恋爱女鬼”,使女鬼重新成为主角的私有物,要么只能被视作危险之物直接消灭。
在“诱惑”之外,“力量”则构成了引发恐惧感的另一重异质性要素无论是“女巫”还是“女鬼”,她们往往被指控拥有来自日常之外的某种神秘力量这意味着,原本羸弱的女性在死亡之后却拥有了暴力性的力量,并对日常世界造成灾难性的伤害。
例如在《纸人》中,生前受人摆布郁郁而终的殷夫人在死后却化为厉鬼挖出殷老爷的心脏在此类由“怜女”向“厉鬼”的转化中所呈现的正是经由“力量”这一中介物,女性得以由“天使(Angel)”向“魔鬼(Monster)”转化。
在传统的两性秩序框架下,这一过程并非意味着只有化身为“魔鬼”才拥有“力量”,恰恰相反,它昭示着这样一种伦理:当女性拥有了不可控的“力量”后,她就化身为了“魔鬼”马克·费舍尔曾在《怪异与阴森》中对“怪异”与“阴森”这两种恐怖形态进行区分:“构成怪异的是一种在场——不属于这里的事物的在场。
而阴森则是由一种‘在场的失败’或‘不在场的失败’构成当不该在场的东西存在,或应该在场的东西却不存在,阴森感就会由此袭来”费舍尔的理论中,“怪异”来源于某种未知外部的侵入,而“阴森”则肇始于空间内部的失衡。
费舍尔对“阴森”的解释恰好契合了有关中式恐怖的另一种定义:“日常的非日常化”,即空间内部并未出现任何来自外界的未知入侵者,而是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空间本身出现了秩序的失衡“女鬼”正是这样一种颠倒、失衡的日常,或许“女鬼”的真正恐怖之处就在于,一个强大的、诱惑的、带有强烈攻击性的女性本身就是“非日常”的象征。
在此意义上,对“女鬼”的恐惧从来不意味着某种普遍化的情绪,相反,它从诞生之初起就嵌入了深深的性别烙印或许我们可以说,对于传统的父权制社会而言,“女鬼”本身就是那些它试图从女性身上驱逐的异质要素的形象化,它们共同塑造了一具蕴含着颠覆性力量的危险身体。
而“对女鬼的叙事”则是对其异质性进行“驱魔”的过程,或者如弗洛伊德所说,是通过“幻想”对危险之物进行的符号性消除在分析欧洲15至18世纪的猎巫运动时,费代里奇指出:“新生的资产阶级需要贬低女性的性和愉悦。
性欲、性吸引力,这些在政治精英的眼中,都被视为无法控制的力量”“驱魔”正是依靠对女巫的惩戒来否认其颠覆性的潜能通过“驱魔”,传统社会得以将女巫身体的异质性彻底拔除,从而将其重新纳入日常的社会秩序中那些拒绝“忏悔”的女性则在公开审判与示众处罚后被处以死刑。
值得关注的是,“驱魔”也恰好是中式恐怖游戏的核心环节玩家的游戏过程便是对异质空间的驱魔过程,玩家的驱魔方式也同样应和着猎巫的两种手段:“毁灭”或“净化”正如前文所述,在《港诡实录》、《纸人》等带有动作要素的游戏中,“驱魔”通常以对女鬼的肉体“毁灭”来完成,而在更多的中式恐怖游戏中,“解谜”构成了游戏的主要玩法。
解谜意味着玩家需要在游戏过程中不断解开谜题,收集线索,以此还原事件背后的真相,即通过对空间内部创伤事件的再发掘达到驱魔的目的当被压抑的真相为玩家所揭示时,闹鬼的空间也会再度复归为日常的空间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玩家的解谜过程正是对女鬼的“净化”过程。
相较于肉体消灭,“净化”则意味着玩家通过更加温情的方式来完成对女鬼危险性的祛除无论是古典志怪,还是当代的恐怖电影、恐怖游戏,解谜通常都呈现为对“真凶”的搜查——当真相被发掘出来后,因怨而死的女鬼要么怨气散尽离开人间,要么在完成对真凶的复仇后彻底消失。
这一逻辑构成了中式恐怖中常有的“冤有头、债有主”模式,即通过将玩家设置为一个处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外的“公正裁决者”形象,女鬼身上的颠覆性力量也被重新收纳进日常秩序的一部分之中。但这一叙事的欺骗性
快来体验【星界云手机】,打破游戏的局限!云端托管手游,挂机脚本助力,让你在游戏中轻松突破,智能操作无限畅快。解放你的双手,成就游戏中的传奇人生!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图片均来自互联网,一切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
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邮箱:631580315@qq.com